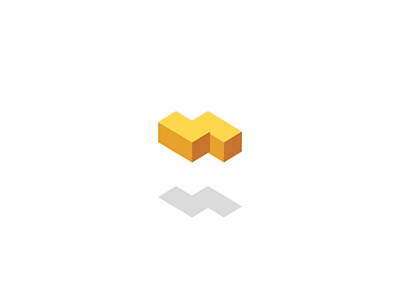7月3日,一则“机器人指挥韩国釜山爱乐乐团”的新闻不胫而走。排练厅里,乐手正襟危坐,指挥台上是一名人类指挥家和一个有着人体轮廓、手部拿着一根指挥棒的机器人。随着机器人挥动指挥棒,台下的乐手也开始了演奏。
开发这项技术的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的李栋旭认为,这个演出是探讨“让机器人能否在创意领域走得多远,并且会遇到什么挑战”。
好吧,作为多年来一直热爱古典音乐,并且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各种录音制品的乐迷,我对此难以理解,至少不会在有生之年买一张由机器人指挥的演出录音,也不会浪费时间去看一场由机器人担任指挥的音乐会。
挥舞着指挥棒并不意味着在“指挥”乐团。如果一根挥动的棍子就能带动一个乐团的话,那么指挥台上摆个节拍器就完事了。乐迷们和音乐爱好者们愿意掏钱买单的,并不是为了一根挥动的金属棒,而是“指挥”在传达背后发挥的真正作用。
但机器人指挥家的出现,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 不只是打拍子
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的录音合集,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如果按照我自己的估算,我手头上就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不下百来个指挥家的CD。而同一个指挥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演绎同一部作品,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效果。譬如,上世纪30-50年代,担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的威尔海姆·富尔特文格勒,在二战时期好几次指挥的“贝九”,就和战后的“贝九”氛围和艺术效果完全不同。
威尔海姆·富尔特文格勒
大概从小学6年级起,我对美声唱法入迷,进而开始探索古典音乐的汪洋大海,到了高中的时候觉得人的声带的表现力实在有限,而交响乐团却通过人的耳朵给大脑赠予了一个宇宙星辰那样浩瀚精彩的精神世界。就好像米兰·昆德拉所言,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宇宙,而每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宇宙。如果说作曲家是这个小宇宙的总设计师,那么指挥家就是绘制这个小宇宙图景的画师。
在音乐会上,人们看到的指挥家,只是在台上挥动着金属棒。但是人们看不到的是,在排练时或者在与乐团的工作相处中,指挥家传递何种艺术理念。从意大利指挥泰斗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严格训练甚至高声责骂,到德国犹太指挥布鲁诺·瓦尔特对乐手们的循循善诱,再到卡拉扬在排练和录音中的一丝不苟,乃至伯恩斯坦在演出中的即兴高潮,交响乐声背后传递的是人的情感,充满的是人的温度。
伯恩斯坦
到了这个层面,指挥家是否拿着一根棍子打拍子已经不重要,指挥的工作本质上,并不是在台上跟着节拍比划,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与乐手的交流,把自己的理念和情感灌输给乐团。譬如,小泽征尔很可能会把自己甩动的头发也作为指挥的工具之一;而“90后”加拿大钢琴家扬·李谢茨基在一边弹钢琴一边指挥乐团的时候,给乐手打个眼色就能产生特别的效果。在管理更加扁平化的21世纪,可能对于李谢茨基这一代年轻音乐家来说,指挥这个角色与其说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统帅”,还不如说是一个“仲裁者”,在乐手之间发挥平衡作用。用歌德形容室内乐作品的本质来说,已经是“几个理智的人之间的对话”。
2 当技术帮助艺术
在20世纪,随着录音和广播技术的发展,包括指挥家在内的许多音乐家得以留下了自己的声音档案。这些经过商业或者未经商业打包出售的黑胶唱片或者CD,能把指挥家和乐团在某一个时段的特质保存下来,颇有艺术价值。
黑胶唱片
就好像所有技术出现的时候,都有人担心它会取代某个行业或者让某些行业质量大打折扣那样,录音技术和唱片工业在音乐界也有反对者。被称作“指挥怪杰”的罗马尼亚指挥家切利比达克就非常厌恶录音,认为每一场演出都是一个独特的精神交流层面,是录音技术难以复制的创作过程。这位语出惊人的大师还用“看着色情杂志手淫来取代做爱”,来比喻用听唱片或者广播的方式取代现场欣赏音乐会。
诚然,切利比达克对指挥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放在整个音乐圈看,他的观点只能属于少数派。也是多得唱片公司在他去世后违反他的意愿,把他过去在现场演出的广播档案制作成唱片,才让他身后的声望比生前高这么多。
对于大部分指挥家而言,20世纪的技术进步帮助他们在事业上和收入上取得了19世纪的同行们难以想象的成就。在二战时期,因为立场反法西斯而被迫流亡美国的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利用当时美国发达的电台广播网络开设了一档在周六固定举行的录音室音乐会,在北美的土地上培养出一大批古典音乐爱好者。
在那个唱片业蒸蒸日上的年代,美国这个本来被老欧洲人讥为“文化沙漠”的国度,迎来了井喷式的交响乐团蓬勃面貌。美国的经济规模非单个欧洲国家可比,二战结束后美国本土的交响乐团质量直追遭到战火摧残的欧洲老牌乐团,不同的美国城市也迎来了不同的乐团风格:费城交响乐团有着北美最醇厚的俄罗斯东欧特色;芝加哥交响乐团难以匹敌的铜管乐组非常适合演绎浪漫主义晚期作品;波士顿交响乐团曾经是法国流派作品的演绎权威;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则是德国-奥地利古典作品的标杆;最老牌的纽约爱乐乐团和在70年代才崛起的洛杉矶爱乐乐团则见证了美国不少本土作品的首演。
纽约爱乐乐团
在50—70年代,那些来自老欧洲,特别是身上流着犹太血液的指挥家,本来可能葬身于纳粹集中营,却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在美国重新打出了一片天。在我刚听古典音乐的那个阶段,我记住了指挥家们跟唱片公司的对标关系:执掌芝加哥的匈牙利大师弗里茨·莱纳就是RCA公司的;同样属匈牙利犹太系的乔治·塞尔则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
但最善用唱片技术获得商业利益的指挥家,也许是柏林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赫贝特·冯·卡拉扬。卡拉扬那张满头银发、身穿燕尾服拿着指挥棒的侧面照片,已经成为了许多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对“指挥家”的仅有印象。我很反感有些人给他“指挥帝王”的标签,但在市场价值上卡拉扬的确成就斐然。到1989年去世时,卡拉扬已经发行了2亿套专辑,给遗孀留下了2.5亿欧元的遗产,包括指挥大师生前钟爱的名车、私人飞机和游艇。
3 谁是下个幸运儿?
爱钻研技术、喜欢摆弄各种机器和飙车的指挥大师,身上似乎有着鲜明的现代特性。卡拉扬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壮年时期正值唱片工业大步前进的时期,到了晚年又遇上镭射唱片技术(也就是CD)出现的风口期,他的许多指挥艺术结晶得以以高质量的录音保存下来。那些比他年长许多年的老大师,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托斯卡尼尼在录制唱片的时候,被录音师喊停了,原因是乐团的起伏过于强烈,会导致机器失灵。“那就让机器爆炸去吧!我的艺术就是要这样!”托斯卡尼尼的怒吼,也反映出大师对那个时代技术的无奈。
托斯卡尼尼
对了,有的乐迷大概还记得,那张年迈的卡拉扬拿着一张CD唱片跟索尼公司董事长侃侃而谈的照片。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卡拉扬的老东家德意志唱片公司刚开始不愿意砸钱投产制作CD,卡拉扬要挟转投签约索尼,倒逼德意志唱片公司研发CD业务。
今时今日,德意志唱片公司还真的要感谢卡拉扬当年的倒逼。卡拉扬生命最后10年用CD技术重新录制的“金碟”专辑,再加上黑胶重新翻录的上百万张唱片等资产,保证了公司在唱片业乃至音乐行业整体走下坡路的时期,有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
如果说卡拉扬是指挥艺术和录音科技结合的巅峰,那么他的去世则标志着分水岭。由卡拉扬栽培的一众“中生代”指挥家,譬如小泽征尔、阿巴多、穆蒂和梅塔等人,在90年代和千禧年前后一度头戴着“明星指挥家”的光环,但始终再也没有创造出类似卡拉扬这样体量庞大的商业奇迹。
柏林古典音乐流媒体“IDAGIO”可以听“柏林爱乐”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指挥家们和乐团管理层一直在摸索下一波科技创新带来的机遇。譬如,柏林爱乐乐团利用网络技术打造出一个需要付费的“电子音乐厅”平台,又或者是其他一些乐团和指挥家先发制人和在线流媒体打响自己品牌。
人工智能也许能成为下一波辅助而不是取代交响乐团和指挥家的科技。譬如,一些身体有严重残障的人士,也许能借助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达成当指挥家的心愿?正如唱片技术让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远离古典音乐发源地的人进入它的浩瀚世界,我也期待新一波技术能够让更多的人群享受音乐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