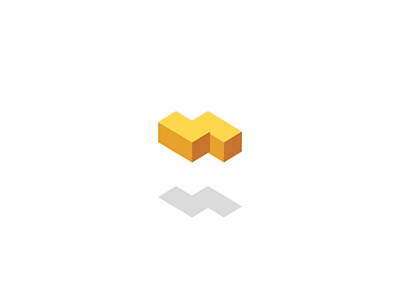1998年春晚,扎着丸子头的王菲牵着十分接地气的那英,完成了华语女歌手对唱的经典——《相约98》。那一年,是她们歌手生涯的巅峰。王菲《唱游》专辑里有长期霸占KTV点播榜的《红豆》;那英凭借专辑《征服》一举奠定内地歌坛一姐地位。
强强联合,成就了《相约98》。“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这是和未来的约定,充满着希望和梦想。
虽然一年前的金融危机雷雨未退,刘欢的《从头再来》仍在街头巷尾传唱。但现实的中国,不只歌声充满希望,一些在广阔市场中尝到甜头的企业,已经开始抬头远望,想让梦想照进现实。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内的通信设备企业。
1998年,大唐电信上市。在此之前,中兴、华为、巨龙已经先后成立。经过几年在程控交换机领域的攻城掠地,四家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在通信设备领域的标杆。华为销售额达到89亿元,中兴为41亿元,巨龙为26亿元,刚成立的大唐也有9亿元。即便是销售额最小的大唐,其利润也超亿元。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欣慰之余,分别取了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第一个字,叫响了通信领域的“巨大中华”。
中兴、华为,诞生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巨龙和大唐则成立于政治资源丰富的北京。两南两北,代表了几种不同结构和风格的公司。20年后,他们的命运也南辕北辙。
巨龙通信在成立后经过了多次重组,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大唐电信在3G时代后,步步走向衰落,在2018年与烽火通信合并成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中兴通讯在缴纳了14亿美元罚款后,2018年全年巨亏69.8亿元。与此同时,唯一的纯民企华为,如今却成为国内科技企业的代言人,全年营收7212亿元,利润593亿元。
命途的迥异,并不是偶然。一切,从“巨大中华”开始传颂的时候,就已经注定。
起步1990年以前,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被七个国家八种制式的产品垄断,称为“七国八制”。从农话到国家骨干电话网,无一幸免。
垄断造成程控交换机的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了安装电话的价格。当时装电话需要交纳大约5000元的初装费,还不包括几百块的电话机钱,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不过200元。当然,有钱还不一定能装上,需要送礼、托关系、批条子。剩下的,就是等。有的外商到大陆投资,公司的电话排了9个月也没装上。
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一批国内企业参与进来。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座右铭,让其中的企业天生对赚钱的生意嗅觉灵敏,率先参与进来。当然,有心归有心,实力就另说了,真正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当时的铁饭碗里。
1985年,43岁的原西安691厂技术科长侯为贵受命在深圳成立了中兴半导体公司。他带领创业初期的38个人在沙河草丛中的厂房里加工电子表、电子琴和电话机。虽然挣了35万块钱,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但是实打实的辛苦钱。
在做电话机生意的过程中,侯为贵意识到电话通信利润丰厚,于是组织人手研制小型程控电话交换机。1987年,中兴第一款产品,ZX-60模拟空分用户小交换机,获得邮电部入网许可。
中兴第一款产品开始进入电信领域的时候,44岁的军转干部任正非由于在南油集团下属电子公司经营中被骗200万元,被迫“下海”。带着身上仅有的几千块钱,这位离异中年大叔在南油新村的居民楼里创立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的介绍,任正非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经过几年的积累,任正非赚了第一桶金。本想狠狠地挣钱,可拿到订单,HAX交换机却经常供不上货。没办法,华为开始着手从国内企业买散件,自己组装、贴牌24门的小模拟交换机,取名BH01。
任正非在被骗前其实还算命好,他转业被分配到的南油集团是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而另一名军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1985年,32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青年教师邬江兴正带着他的团队研发每秒5亿次运算速度计算机DP300系统。万万没想到,就在项目攻关的关键期,裁军100万,项目在裁减之列,几年心血被锁进柜子。
一切戛然而止,空有一身本领的邬江兴干什么成了大问题。后来,学校的校办工厂没有项目,领导对邬江兴提议,你们去搞搞程控交换机吧。虽然觉得交换机没有计算机高大上,但是作为军人,只能服从。邬江兴于是带领团队的15个人,拿着向领导借来的15万元,开始了程控交换机的研发。
当大家还在交换机领域摸索的时候,1986年,原邮电部邮电研究院(大唐电信的前身)一所就已经研制出了20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DS-2000。没过多久,邬江兴的团队也实验成功了一台千门的模拟程控交换机。与中兴、华为在研的60门和24门模拟交换机相比,产品规模和难度简直是鸿鹄与燕雀。
再把比较面扩大,彼时所有成果和努力与真正的需求和国外的水平相比,同样是天上地下。中国爆发的电话市场真正需要的是万门以上的数字程控交换机。1982年,福州就引进了国内第一台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日本富士通的F-150,引起轰动。邬江兴后来去参观,“他们不让看。好说歹说,只能在机房外隔着玻璃看,跟看猴儿似的。”[3]相应的研发能力的确还不具备,有外国设备商直接断言:“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交换机”。
外国厂商得意之时,国内各路人马已经悄悄集结完毕,默默等待开花。然后,“我花开后百花杀”。
辉煌自从邬江兴在福州被玻璃墙挡在心仪的万门程控交换机之外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做一个万门机给老外看看。可空有热血和激情造不出东西,科研是严肃的事,也是很现实的事。国外研发万门程控机动辄需要投入几亿美元,动用几千人花好几年才能完成。邬江兴一没钱、二没人。
好在第一次研发出千门交换机之后,逐渐有了一些名气。业内开始知道郑州有一帮人能做程控交换机。对于当时巨大的市场和无法自主可控的现状来说,这点名气很重要,也很及时。后来,邮电总公司投资600万,让邬江兴他们试试大一点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团队另辟蹊径,抛开了传统的交换机架构,从封存的大型计算机系统中寻找灵感。结果,成功了。1991年11月,邬江兴和同事们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通过鉴定,这就是著名的“04机”。
“04机”的出不仅填补了国产程控交换机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长了国人志气。1992年,贝尔公司外方总经理专门到河南武陟实验局考察,“他很震惊,自言自语地说未来将是04机的天下。”“04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的争气机”。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难掩激动,批示道:“在国有企业纷纷与外资合营或被收买兼并后,04机送来了一股清风。”
与此同时,邮电研究院十所在DS-2000的基础上,用传统的方法和思路实现的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DS-30也通过鉴定。两家北方的企业搞得红红火火,处在南国深圳的中兴和华为却刚刚起步。
中兴成功研发ZX-60后,侯为贵力排众议,用外贸挣来的钱集中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1990年,中兴研发的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中兴也正式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
1991年,任正非说服本来要去清华读博士的华工老师郑宝用,在蚝业村工业大厦三层用一年时间开发出了HJD-4848门交换机。在那里,他们吃喝拉撒睡全在公司,也因此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床垫文化”。很快,HJD-48迅速延伸出了100-500门的系列化产品。
到了1992年,凭借ZX-500和HJD-48500门交换机,中兴和华为的产值双双突破1亿元,利润分别超过2000和1000多万元。有了钱,两家公司旋即又投入了新产品的研发。
一年后,由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属第十研究所和朱亚农博士在美国创办的国际电话数据传输公司(ITTI)公司共同组建的西安大唐电信成立。公司以DS-30万门交换机为基础,注入ITTI的技术,开始研发全新的数字程控交换机SP-30。
而此时,“04机”凭借先发和技术优势,再加上政府和军队背书,已经全面在国内铺开,并很快就进入了大中城市。一时间,国内电信设备市场刮起了一股“04机”风潮,邬江兴的团队最多要同时派十几个安装小组北上南下,最快的23个小时就安装开通一个电话局。及至1995年,04机在全国已经部署了1300万线之多,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
趁热打铁,由“04机”技术持有方与另外8家生产企业共同出资,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1995年3月在北京注册成立,邬江兴担任董事长兼总裁。
这边巨龙风光无限,那边其他公司也没闲着,技术迭代开始加快。
1993年,虽然华为费劲全力开发出来的模拟交换机JK1000刚做出来就基本被淘汰了,但任正非毫不犹豫地又启动了新的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项目。所谓C&C,有两个含义:一是 Country & City(农村&城市),华为希望从农村走向城市;二是Computer & 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代表数字程控交换机采用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4]。
起初的C&C08 A型机容量仅为2000门,但总工郑宝用提前布局,在研发A型机的同时,让不到22岁的天才实习生李一男负责万门C型机的方案设计。光物理专业毕业的李一男提出了用准SDH技术(一种光纤传输技术)将多个模块连接起来的实现方案。1994年8月,基于该方案的万门机C&C08 C型机研发成功,并在江苏邳州顺利开局。
此后一年,是国产万门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丰收年。6月,西安大唐电信研发的SP30数字程控交换机通过了邮电部组织的鉴定,最高可扩展至40万门。11月,中兴研制的ZXJ10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入网许可证。
凭借自主技术、优质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国产大容量程控交换机开始大规模占领市场。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七国八制”的程控数字交换机价格开始直线下跌,单位价格从500美元、300美元、100美元直至30美元。七国公司还反应过来,就开始从一路领跑变成被动追赶,直到被国内厂商远远地甩在身后。
对于老百姓来说,好处显而易见。装电话不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了,电话装机费用一降再降,最终成为免费。电话在中国普及,不过用了五六年时间。
及至1998年9月,集合了西安大唐电信、十所等优质资源的大唐电信集团成立。“巨大中华”已经成为中国通信行业的代名词,一路高歌猛进。仅巨龙一家的04交换机,已经占到全国网上运行交换机总量的14%。
然而,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几家公司车轮下的轨道已经悄悄转向分化,只待鸣响汽笛。
转折1998年,巨龙制定的国际市场三年计划提前完成,“04机”卖到了朝鲜、俄罗斯、古巴、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出口额1000多万美元。邬江兴不无激动地说:“04机开始了技术和产品出口的新阶段,实现了国产交换机产业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正当邬江兴憧憬国外市场时,巨龙的国内销量却开始进入了平台期。在有些县市,电信部门甚至开始逐步拆除“04机”,换上更先进的交换机。替换的原因很简单,“04机”的技术一直在原地踏步。如果没有其他厂商的群体突破也就罢了,可是别人在不断进步,你不动,就是退步。
退步的原因,在几年前就埋下了伏笔。巨龙的“04机”投入商用后,是通过信息工程大学授权给8家老国有通信厂同时进行生产。作为技术提供方的信息工程大学由于身份特殊,实际上没办法直接参与经营,游离于企业管理之外。而集团对8家生产厂的控制有限,导致各厂商迅速陷入了短期利益的争夺。
“04机”不仅要面对华为、中兴的竞争,还要面对自己人的竞争。在常州的邮电会议上,代表北京738厂的巨龙销售一进门,不仅看到了华为、中兴的人,还看到了同属巨龙的洛阳537、杭州522的销售。各厂商为了自己的销量,哪里记得同属一家,直接拿起价格屠刀,开始杀价。
产权和经营权的混乱使整个巨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开始脱节,战略无法统一,价格各自为战,研发停滞不前。巨龙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996年,巨龙就已经实施了第一次资产重组,主要调整了内部股权比例和经营层。不过,当时正值大容量交换机市场的爆发期,销售量一路攀升使得更深层次的各企业关系、股东和管理层的分工、研发力量外置等等关键问题被轻易地忽略了。
到了1998年,表面红红火火的巨龙内部已经千疮百孔。面对1.5人的巨型企业,没人关心管理、研发和市场,都在谈论一件事:哪家企业会占上风,谁会出任总经理?有员工调侃道:“我得记录下来,巨龙的事足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9年,军方不允许参与市场经营,部队方面的技术团队退出巨龙,研发力量受到重创。6月,灵魂人物邬江兴辞去董事长职务,回到信息工程大学,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巨龙从此一蹶不振。
巨龙暗潮涌动的1998年10月,刚刚组建一个月的大唐电信风风光光地上市了。相比巨龙,大唐虽然也是由多个研究所和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但它实际上受电信科学研究院直接领导,研发、生产、销售统一。更值得称颂的是,大唐在90年代末就针对未来的无线通信提出了TD-SCDMA。技术过硬,又有国家站台背书,实力雄厚。
皆大欢喜的日子,居然有人愁。作为集团主体的西安大唐电信的总经理朱亚农在上市前被罢免。到了上市时,朱亚农只得到了一个副董事长的虚职。
类似的故事在大唐电信并不是个案。同样是在上市前,大唐投资的信威科技董事会把创始之一的陈卫炒了鱿鱼。信威科技是后来大唐引以为傲的TD-SCDMA标准早期研发单位。虽然陈卫后来又回到信威,但已然错过公司最佳的发展期。
现在半导体学术和产业分析领域炙手可热的清华魏少军教授,在1998年还是大唐微电子中心的负责人。彼时,他带领团队推出的IC电话卡芯片让全国为之一振。他也因此一路升迁到大唐电信总经理和大唐微电子董事长。没想到几年后,魏少军在正当打的年纪突然从大唐全身而退,进入学术界搞研究,令人唏嘘不已。
在后来的3G标准战,大唐并没有逃出成立时的怪现状,战略缺乏传承、核心业务的分解、内部的斗争使大唐并没有抓住TD-SCDMA的红利,反而一误再误。2017年,曾掌舵大唐电信10年的真才基落马,一切为时已晚。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折腾。
回溯到1998年,国企改革步入深水区,大唐上市,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关朱亚农还有其他的问题,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当年的巨龙和大唐,正值人生巅峰。他们一路风光无限,却忽略了顶峰另一面的悬崖。与此同时,华为中兴却从管理开始入手,自我变革,开始了自底向上的逆袭之路。
1997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1998年,中兴的员工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但管理却是5年前只有600人时制定的,很多问题随着员工数的膨胀和产品的多样化不断出现。
侯为贵认为这是管理边界不清晰导致的。在他的主导下,1998年1月,中兴撤消了公司原有的职能机构、部门,实行准事业部制。“在管理上实行分权与集权的优化统一,明晰管理层次;强化利益机制;强化公司职能管理;密切开发、生产、市场3个环节的关系”。
其中的核心其实只有两个,管理分层和利益驱动。管理分层其实就是把公司的总体技术、产品规划上升,把具体的项目研发、制造和测试下沉,统一协调各部门、各项目的资源。利益驱动则是明确了产品总经理掌握研发资金,同时对产品利润负责。这样,有了绩效指标和资源支配权的产品总经理,就成为了一个个基础的效益引擎,推动整个公司的发展。
此时,华为的分层式矩阵管理体系已经施行了近三年,但管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当时的DECT无线基站项目经过三年没头苍蝇般的艰苦研发,最终产品只能躺在实验室里,上千万的研发费用打了水漂。
内生的变革已经无法满足华为的需求了。任正非认为需要用外部的力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世界发达国家先进公司已经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前进,这样我们就占了很大便宜,我们的生命就能放射光芒”[7]。
1998年3月,人大教授彭剑锋等十人历时三年多为华为制定的文化和管理基础《华为基本法》颁布。8月,华为召开动员誓师大会,宣布花费5000万美元全面引进IBM的IPD系统。将管理进一步细节化、标准化、流程化。任正非号召“向IBM学习”,让50多位西装革履的IBM洋顾问成为各核心部门的老师,开始全面的培训和重点实践。他说:“IPD要培训、培训、再培训,让考试不合格者下岗!”
以1998年为起始,华为开始了全面学习西方管理经验的过程。除了IPD,后来又花费几十亿元引进了IBM的ISC(集成供应链)系统和IFS(集成财务服务)系统、美世咨询的EMT(经营管理团队)系统、Hay Group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等西方管理系统。
这些先进的管理体系,让华为真正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拥有了成熟且有效的管理模式、流程和方法,为今后管理十几万人的航空母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98年的换机潮中,那些替换“04机”的,正是华为的C&C08。一车车拆下的“04机”被运往更为偏远的农村,这与华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恰恰相反,成为当时这些企业命运的写照。
从此,巨龙远去,华为归来,“巨大中华”分道扬镳。
根源“巨大中华”在1998年经历的变革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比赛。奇怪的是,通常让各大公司头疼的市场、资金问题却并不是这场比赛胜负的决定因素。
有“04机”的盛誉和国企身份背书,巨龙、大唐更多的时候是客户找上门来,甚至有时候可以从政府直接拿订单。而华为、中兴在起步阶段连听说过的人都很少,见大客户真的要挤破脑门。不得已,他们只能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点点把市场和品牌培育起来。
在资金方面,1998年,巨龙成为第一个得到国内买方信贷政策支持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获得建行、工行总计55亿元的额度支持[8]。而此前任正非孤注一掷地投入C&C08研发的时候,华为账上已经快没钱了。那时中小企业的境遇和现在也没什么区别,他从银行贷不到款。没办法,只能去借高利贷,压力大得时常把“跳楼”挂在嘴边。
有市场和资金的国企逐渐没落,只能一点点磨客户的没钱小公司却一骑绝尘。这一切表面上似乎源于1998年各家企业经管上发生的变革,实则有更深的内因。
首先,是产权和经营权问题。巨龙没落的原因之一就是产权不清,没有统一规划,各家企业各自为政,造成资本、经管和研发严重脱节。灵魂人物邬江兴退出后,群龙无首,各方斗争更加激烈,直至衰败。
巨龙的遇到的问题也曾困扰着侯为贵。中兴半导体成立时,由691厂、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及其隶属航天部的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出资280万元,成为深圳特区最早的一批技术类合资公司之一。后来公司挣了钱,股东间却由于分红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效率。
1992年,航天部领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实在不行你们可以自己出来干”,让焦头烂额的侯为贵茅塞顿开。第二年,创业元老们创建的中兴维先通公司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进行了第一次重组,成立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这是深圳第一批股权清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之一。
鉴于之前的教训,新董事会明确两家国有企业不参与运营;由中兴维先通承担经营责任,保证国有资产增值,若出现经营不善,则需用股本进行补偿。中兴在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即“国企民营”的全新模式。侯为贵被任命为总经理,企业的经营由他说了算。困扰巨龙和当时许多企业家的产权、经营权问题在中兴就此解决。
而华为更进一步,不仅要解决谁说的算的问题,更要防止一言堂。作为纯民营企业,华为采用全员持股的方式,股东数量接近9.7万人。虽然任正非的股权只有1.01%,但他已经成为公司的图腾。当然,有当年在手机、小灵通业务上失策的前车之鉴,为防止再次因为任正非的个人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公司在2003年引入EMT(经营管理团队)系统,大事需要有8位高管集体决策。2011年,华为开始采用轮值主席制度,进一步分散权力。
其次,是人才问题。所有的业绩,都是靠人干出来的。尤其在通信等科技产业里,需要科学家、工程师、产业工人等形成的人才梯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就事业。
在“巨大中华”开始起步的80年末、90年代初,高校、国有企业是真正的人才聚集地。大学和大厂,都是金子招牌。最早的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能够诞生在巨龙和大唐,不是没有原因的。
彼时的华为和中兴,根本没人知道这两个的小公司是干什么的,更别提吸引人才了。为解决这问题,任正非广泛邀请高校教授带队到公司参观、合作,再通过师生、同门的关系组建了早期的研发队伍。例如华科的青教郭平跟着老师来参观,被任正非的激情感染留了下来。他后来拉来了同学郑宝用,郑宝用又叫来了师弟李一男。
可这样的方法效率还是太低,根本满足不了企业高速发展的人才问题。于是任正非开始想方设法挖同行墙角。华为最初的产品与电信十所(西安大唐的前身)有合作,任正非就给那些从十所过来的员工一个任务,每年过年回家要带几个前同事到华为来。另外,邮电部在西安举办程控交换机学习班,来的都是各单位的技术骨干,华为的学员白天学习,晚上就跑到各个宿舍去挖人。因为对人才的渴求,华为没放过每一个发掘、吸引人才的机会。
反观大唐,高层的朱亚农、陈卫和魏少军们,或郁郁不得志,或黯然离场,基层的技术人员则被不断挖角,人才流失严重。
最后,是激励的问题。人才来了,如何留住人才,创造价值,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郭平刚到华为就被任正非委以重任,成为HJD48的项目经理。李一男七天就当上了高级工程师,负责万门机的研发;不到一年成为交换机产品总经理;两年后,成为公司副总裁;再过一年,升任研发一把手。这种速度,这是对真正人才的珍惜和信任。
但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每一个员工的激情和梦想是没办法持续的。单靠委以重任的信任、热血沸腾的参与感和产品成功的成就感依然不是长久之计。如何有效激励员工,才是考验公司和企业家智慧的关键。
在大唐这样的国企,每一层级的负责人都有对标的行政级别。个人升迁往往是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升迁要政绩,因此那些短期见效的政策备受追捧。于是一任领导一波政策,左右摇摆,机遇就此从指间溜走。长此以往,造成公司的导向颠倒,层层向上负责,而不是对客户、团队、产品和利润负责。
对于普通员工,受工资总额的限制,多干、少干一个样,操心、不操心也一个样。付出和所得的巨大反差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有能力的纷纷因为待遇不公而出走。早年华为、中兴能够从西安大唐、电信研究院挖走大量的人才正是找到了这些“良币”的痛点。
中兴在1998年的改革就是明确了项目经理的绩效指标和权力,从而激发了这一层级的工作积极性。不过,激励机制也仅到达这一层。更让人惋惜的是,在经过股改、上市后的20多年的发展,直到去年中兴事件爆发,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利益导向没有进一步下沉到基层,反而向高层输送。侯为贵和其他高层通过维先通持有中兴通讯约15%的股份。而其60多家子公司和10多家联合经营的企业,股东多是中兴通讯高管和骨干,对子公司业绩好坏的关心往往大过中兴通讯本身。
华为则通过全员持股,很早就把“钱程”和个人在企业中的发展前程与企业的成功、产品的成败绑在一起,解决了大家为谁奋斗的问题。任正非曾说过:“传统上,职工参加了劳动就不能‘所有’企业,而资本只能雇佣劳动,不能反过来;早期的华为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连起来了,华为的突破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中间联结点,把知识和产权连起来,而且在不断变动”。“狼性”是用鞭子抽不出来的,激励到位,每个人都会露出獠牙。
企业的产权和运营机制解决的是短期利益分配问题;人才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潜力;而具有正向激励的人才机制则提供了企业发展的长期驱动力。时光回到1998年,“巨大中华”在这些问题上的状态和政策已经非常明晰,二十年后的命运也因此注定。
尾声2018年春晚,王菲和那英时隔二十年再次登台,演唱了一首《岁月》。二十年时间,一盒磁带已经哑然失声;一本书已经开始泛黄;一张照片已经变得斑驳;一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很多人相约20年后再见,却再也不见。
20年前,“巨大中华”也作为国家通信设备产业的标杆,被人们称颂。所有人都觉得那种突进狂飙的发展是一种常态。“巨大中华”四个字就像四家公司的约定,相约的不止是二十年后再见,而是做“百年老店”。
但很多人都忘了,自古帝王将相都在寻找抵御时间的力量,结果通通失败了。原因在于什么?在于过度自信,忽略了历史的进程和自身的问题。
公司也一样,回过头来看,交换机厂商的发展是与当时国内电话业务的爆发相辅相成的。而“巨大中华”在1998年发生的故事,对环境和自身的认知可见一斑。巨龙忙着内斗,大唐急着上市圈钱,中兴在做分层管理改革,而华为不仅出台了“基本法”还引进了国外的管理体系,至今仍在“坚定不移地向美国学习”。
如果再把眼光拉高放远,会发现“巨大中华”不是一个特例。很多公司的成功实际上是依靠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腾飞实现的。大环境好,什么都好。营收的高速发展足以掩盖产权、管理、人才和激励等核心问题。但时间是公平的,不仅给了公司查缺补漏的时间,也给了蝼蚁们筑巢打洞的机会。当千里之堤行将崩溃,才想到找政府、找组织、甚至用情怀来裹挟民众,一切都来不及了。
“巨大中华”的命途差异,只是中国众多公司的一个缩影。如同《岁月》里唱的:“云很淡,风很清,任星辰,浮浮沉沉。”
沉浮之间,是理性和智慧使然。
推荐阅读华为启示录:中国制造业的冲击
5G背后的激流暗涌:见证通信巨头的崛起之路
本文已标注来源和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